引言
12月8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深度報道欄目《世界周刊》播出了“韓國娛樂圈自殺魔咒”專題節目,節目指出,短短50天內,三位韓國藝人崔雪莉、具荷拉、車仁河離世。奴隸合同、地獄式工作模式、不成正比的付出與回報、被迫整容、嚴控飲食、網絡欺凌…那些鏡頭前光鮮亮麗的韓國藝人,私底下卻可能經受難以言說的困難。韓國娛樂圈的種種陋象令人瞠目結舌,而在我國,經紀公司與藝人的“相愛相殺”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例如鄧紫棋在今年3月份與合作13年的經紀公司解約,鄧紫棋在社交平臺發文痛斥經紀公司常年使其受不公平待遇,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安排代言,商業演出安排太滿導致原創作品質量下降等等;再如歌手蔡依林為“跳出經紀公司的?坑”支付?額違約?與原經紀公司解約、張杰與上海上騰娛樂公司為解約對簿公堂、“四?天王”之?的劉德華也曾與其經紀公司發?生糾紛,最后?付巨額違約金解約。
在娛樂產業迅速發展的今天,藝人已經成為文化娛樂產業的代表,他們風光無限,他們的粉絲數量可以過億,他們在聚光燈下璀璨奪目。然究其本質而言,藝人是經紀公司包裝的一個“商品”,在流量、人氣與商業利益掛鉤的時代,經紀公司會盡一切辦法實現藝人的商業價值,而經紀合同便是關于如何包裝打造藝人、如何實現藝人商業價值的的書面約定。藝人經紀合同經常被稱為“賣身契”,藝人的人身權利都要受到經紀公司的干涉和安排,而藝人一旦“不聽話”,也有可能被經紀公司封殺或雪藏,藝人即便解約也要承擔高額違約金。因此,選擇一家有實力又靠譜的經紀公司,簽訂一份相對公平合理的經紀合同,對于藝人個人的發展而言是極為重要的。
本文旨在通過分析藝人經紀合同糾紛司法案例,探究藝人經紀合同的性質及司法裁判規則,同時剖析經紀合同中常見的雷區,對藝人簽訂經紀合同時應注意的問題和風險提出合理化建議,以爭取最大限度維護藝人的合法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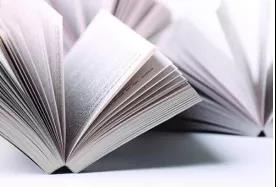
一、藝人經紀合同的概念及分類
關于藝人經紀合同的定義,目前并沒有確定的標準。在《合同法》中,經紀合同并非有名合同,法律上尚未確定一定的名稱與規則。筆者認為,藝人經紀合同就是經紀公司與藝人對演藝?作安排的書面約定,其內容主要包括藝人與經紀公司的合作范圍、內容、方式、期限、利潤分成、雙方權利義務及爭議解決等方面,系包含委托、代理、居間、?紀、以及一定?身屬性的無名合同。
藝人經紀合同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影視演員經紀合同、歌手經紀合同、模特經紀合同、網紅主播經紀合同。后兩者的基本內容比較少,條款與前兩者類似。影視演員經紀合同和歌手經紀合同比較常見,且經紀合同的內容比較全面,涉及的法律問題也較多。例如對于創作型歌手,其經紀合同可能涉及詞曲著作權的歸屬等問題,經紀合同需要包括經紀約、唱片約、詞曲約三方面。因此藝人經紀合同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需要謹慎處理,如果未約定明確,可能為后期經紀合同的履行埋下隱患,對藝人的星途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二、藝人經紀合同的性質
藝人經紀合同的性質一直是理論與實踐中的關鍵問題,綜合部分司法案例的爭議焦點可以看出,藝人經紀合同糾紛爭議焦點之一是經紀合同是否為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一方主體是否可以根據《合同法》第410條的約定主張任意解除權。經紀合同的定性問題將直接決定藝人是否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權,作為藝人一方大多會主張經紀合同屬于委托合同,借此行使任意解除權;但是作為經紀公司一方,則會主張經紀合同屬于無名合同,應適用《合同法》總則的規定,并可以參照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最相類似的規定,藝人不享有任意解除權。
關于經紀合同的定性問題,最高院在熊威、楊洋與北京正合世紀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經紀合同糾紛再審案件((2009)民申字第1203號)中已作出相關認定,最高院認為經紀合同不僅包含關于演出安排的約定,還包含經紀公司對藝人的商業運作、包裝、推廣以及著作權使用許可等多方面內容,而且各部分內容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構成雙方完整的權利義務關系。關于演出安排的條款既非代理性質也非行紀性質,而是綜合性合同中的一部分。割裂該部分條款與合同其他部分的關系,孤立地對該部分條款適用“單方解除”規則,有違合同權利義務的一致性、均衡性及公平性。因此,熊威、楊洋主張其有權依據《合同法》關于代理合同或行紀合同的規定隨時解除涉案經紀合同中演出安排條款的主張不能成立。除此之外,竇驍、林更新、蔣勁夫、張杰等藝人與經紀公司解約糾紛案件中,法院均認定經紀合同是兼具居間、代理、行紀性質的綜合性合同,因此經紀合同當事人不享有任意解除權。
關于為何不能認定為委托代理合同,除了法律層面上經紀合同不符合《合同法》關于委托代理合同的規定之外,司法裁判也同時考慮到演藝行業整體運營秩序的問題,北京高院在竇驍與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合同糾紛((2013)高民終字第1164號)判決中認為“因為在演藝行業中,相關從業人員(即藝人)的價值與其自身知名度、影響力緊密相關,而作為該行業從業人員的經紀公司,在藝人的初期培養、宣傳以及知名度的積累上必然付出商業代價,同時藝人是否能夠達到市場的影響力,存在不確定性,由此經紀公司在藝人的培養過程中存在一定風險。在藝人具有市場知名度后,經紀公司對其付出投入的收益將取決于旗下藝人在接受商業活動中的利潤分配,故若允許藝人行使單方解除權,將使經紀公司在此類合同的履行中處于不對等的合同地位,而且也違背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同時會鼓勵成名藝人為了追求高額收入而惡意解除合同,不利于演藝行業的整體運營秩序的建立,因此在演藝合同中單方解除權應當予以合理限制”。據此,在實踐中藝人如主張以委托人的身份單方解除經紀合同,很難獲得法院的支持。
綜上,結合筆者查閱的其他司法判例中關于經紀合同定性的裁判要點,就目前藝人經紀合同的定性總結如下:《合同法》中并沒有對經紀合同進行歸屬劃分,經紀合同是一種具有綜合性質的新型合同,包含居間合同、委托代理合同、行紀合同、勞動合同等多種合同性質,對于居間、委托、代理、服務、著作權等法律關系作出了明確約定,內容較為復雜和細化,應適用《合同法》總則的規定,將經紀合同作為無名合同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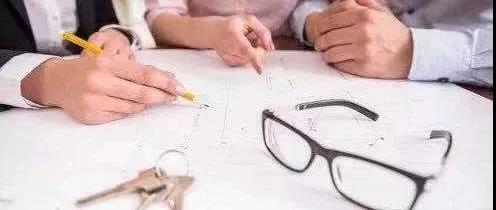
三、藝人經紀合同的司法裁判規則
司法實踐中關于經紀合同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經紀合同的性質問題;二是經紀合同的解除或繼續履行問題;三是雙方是否存在違約行為及違約損失如何計算的問題。其中關于經紀合同的性質問題在上述第二點已作詳細分析,不再贅述。關于另外兩個爭議焦點,筆者查閱大量判決書后,總結如下:
1、經紀合同不屬于委托合同,因此合同一方主體不享有單方解除權,若藝人主張行使任意解除權解除經紀合同,不會得到法院的支持;但若有充分證據證明經紀公司違反合同約定觸發合同解除條款,則藝人可以根據經紀合同的約定行使約定解除權。另外,如藝人能夠提供充分證據證明經紀公司違反《合同法》第94條的規定,則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權。
上海坤宏傳媒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薛之謙其他合同糾紛((2014)靜民一(民)初字第1163號)一案中,法院就薛之謙主張根據經紀合同之約定行使解除權的問題作出如下認定:依據薛之謙與坤宏傳媒公司的的經紀合同約定,坤宏傳媒公司在合約中對薛之謙的承諾未能實現以及坤宏傳媒公司破產或被取消營業資格時,經薛之謙同意,雙方可以提前終止本合約。由于合同的履行是建立在誠實信用、自愿公平的基礎上,有利于原被告共同發展為目的,且雙方對合同的履行應相互信任、積極配合。鑒于坤宏傳媒公司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出現了違約行為,雙方產生了諸多矛盾難以調和,雙方當事人之間已經不具備互相信任的基礎合同關系,薛之謙亦已向坤宏傳媒公司明確表示了終止履行合同的意愿,繼續履行合同已經不利于雙方的利益,弊大于利。故坤宏傳媒公司要求薛之謙繼續履行合同的訴訟請求,未得到法院支持,法院確認系爭合同的解除日期為薛之謙提出解約之日。
而與薛之謙經紀合同糾紛案不同的是蔣勁夫與天津唐人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糾紛((2016)靜03民終13936號)一案,蔣勁夫主張因唐人影視公司存在根本性違約行為,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如拖欠演繹報酬、未提供充足的演繹機會、未履行合同約定的培訓義務、雙方之間的信任基礎已喪失,因此行使法定解除權,解除經紀合同。對此,一、二審法院經審查均認為雙方雖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產生了分歧,但并不存在合同無法履行的法定情形。雙方當事人之間的信任雖是履行合同的重要基礎,但缺乏信任并非享有合同解除權的法定理由。蔣勁夫以缺乏信任為由主張行使合同解除權,于法無據,一、二審法院均未支持蔣勁夫關于合同解除的訴訟請求。
綜上,在藝人提出解約時,如果僅以經紀公司沒有為其提供充足的演藝機會或商業合作,沒有兌現收入或克扣報酬,罔顧藝人的人身安全或聲譽等理由,主張經紀公司已達至根本違約而主張合同解除,可能不被法院支持。只有在經紀合同有明確約定上述情形出現后,藝人享有單方解除權或經紀公司的違約行為導致經紀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時,藝人才有可能解除經紀合同,而非履約過程中經紀公司出現了過錯,藝人就可以解除經紀合同。同時,對經紀公司的違約行為,藝人應承擔舉證責任,否則也可能因為舉證不充分而導致解除合同的訴訟請求無法得到法院支持。
2、關于經紀合同雙方是否存在違約行為以及違約損失如何計算的問題,首先應當根據經紀合同的約定來認定,如經紀合同約定不明確,則可參考《合同法》的規定;違約損失通常包括直接實際損失和合理預期損失,其中法院在認定經紀公司的合理預期損失時,會參考藝人在同類商業活動中的收入酌情處理。
筆者檢索到的案例大部分是因為藝人在經紀合同存續期間,擅自參加其他商業活動,違反經紀合同中關于獨家代理、全權代理的約定,經紀公司因此起訴要求賠償損失的情形。如經紀合同有明確約定的,則可以根據合同約定認定是否存在違約行為及損失的計算方式等。但若經紀合同沒有約定,則法院會根據《合同法》的規定進行認定。在前述蔣勁夫與天津唐人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糾紛一案中,二審法院認為根據《合同法》第107條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根據涉案經紀合同的約定,“唐人影視公司于合約期間作為蔣勁夫的獨家及唯一經理人,而蔣勁夫獨家向唐人影視公司提供蔣勁夫在世界各地與演藝業務有關之服務”、“唐人影視公司在合約期內全權負責代蔣勁夫收取于提供服務之所有收入,于合約期內唐人影視公司抽取蔣勁夫之演藝收入的30%”。故蔣勁夫擅自開展演藝活動,未向唐人影視公司支付傭金,屬于違約行為,應賠償唐人影視公司因此產生的可得利益損失。法院在雙方當事人均未提交充分證據證明蔣勁夫擅自開展演藝經紀活動所取得的收入情況下,參考蔣勁夫在唐人影視公司經紀活動下同種類活動的平均收入水平,酌情確定蔣勁夫向唐人影視公司賠償損失200萬元。
3、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關于上述第2點藝人是否存在違約行為及違約損失的舉證問題,法院傾向于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及《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112條的規定合理分配舉證責任,通常認為雙方均有舉證責任,如雙方證據均不充分,則法院可根據事實情況及現有證據,酌定損失賠償金額。
上海唐人電影制作有限公司訴林更新委托合同糾紛、蔣勁夫與天津唐人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糾紛、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與竇驍表演合同糾紛等判決內容均體現上述裁判規則,筆者以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與竇驍表演合同糾紛為例具體分析如下:
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與竇驍表演合同糾紛((2013)高民終字第1164號)一案中,一審法院將證明是否存在報酬的舉證責任直接歸屬于新畫面公司,認定新畫面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其主張的竇驍擅自參加59項活動均為演藝活動及竇驍的獲酬情況,故對其主張要求竇驍賠償494萬元經濟損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而二審法院就此問題作出改判,認為竇驍關于所參加的59場活動并未獲取報酬的主張顯然與基本的商業慣例及行業常識相違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的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由于竇驍系參加涉案59場演藝活動的當事人,其應當持有相關活動的合同文本,其中對具體活動是否存在報酬以及相應數額應當進行了明確約定,但經法院釋明后,竇驍表示其不持有相關合同文本,且未向法院提交,由此應當根據上述司法解釋作出不利于竇驍的認定,至于新畫面公司上訴要求竇驍因此部分違約行為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494萬元的請求也未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該訴訟請求缺乏事實依據。因此,法院綜合考慮新畫面公司所主張涉案59場活動的性質、規模、以及竇驍作為藝人的知名度、影響力,并且結合竇驍以往接受此類商業活動的酬金情況等方面的因素,最終酌定由竇驍向新畫面公司支付因其在經紀合同期間擅自參加演藝活動所造成的損失人民幣一百萬元。
綜上,因違約導致合同解除,其損失通常按照直接實際損失和合理預期損失計算。實際損失即經紀公司前期對藝人的投入,包括包裝、培養、宣傳、推廣等費用;合理預期損失主要指藝人提前解除合同導致經紀公司預期收益的損失,可以依據藝人因違約行為獲得的收益或者為他人帶來的利益計算,也可以依據藝人的年均收入情況,或者參考藝人在經紀合同期內參加的同類商業活動的收入情況,從而估算經紀公司因解約可能產生的預期收入損失。對于直接實際損失,經紀公司負有舉證責任;對于合理預期損失部分,藝人與經紀公司均有舉證責任,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及《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112條的規定,如藝人和經紀公司的舉證均不充分,則法院傾向于根據藝人參加類似商業活動的酬金情況等酌情處理。
四、藝人經紀合同的“雷區”及“避雷指南”
根據近期代理的明星經紀合同糾紛案件,結合對相關經紀合同糾紛司法裁判案例的匯總分析,對藝人簽訂經紀合同時應注意的“雷區”進行歸納總結,并提出相應的法律建議,以供藝人簽約時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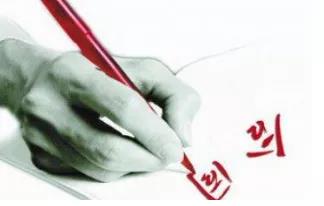
雷區1:獨家條款及超長的合同期限
“獨家條款“通常約定藝人未經經紀公司的同意,不得擅自與任何第三方就本經紀合同所涉范圍、內容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亦不得未經經紀公司同意擅自向第三方提供演藝服務。“獨家條款”會給藝人帶來很大的潛在隱患,通常大家所說的“雪藏”就是“獨家條款”最大的問題所在。如藝人與經紀公司之間有任何問題或嫌隙出現,或經紀公司計劃將主要資源給予其他藝人的時候,那么簽訂“獨家條款”的藝人可能被經紀公司雪藏,且通常情況下經紀合同期限至少3年,可能還會約定期滿后經紀公司有優先續約權,部分經紀合同甚至約定期限長達10年或甚至更長,藝人最黃金的發展時期可能會就此錯過,再與星途無緣了。
避雷指南
簽訂“獨家條款”時,建議同時加入以下條款“若藝人自行獲得其他演藝服務項目,則經紀公司應盡本合同項下同等的勤勉義務為藝人磋商、簽約,并負責宣傳、管理及運作,經紀公司有權提取與本合同項下同樣比例的傭金;若經紀公司未履行前述義務,在藝人書面催告后3日內仍未履行的,則藝人有權自行與第三方簽署相關合作協議,且不視為違反經紀合同約定,無須承擔任何違約責任、損失補償或賠償責任,且經紀公司就藝人因此取得的報酬無權收取任何傭金。
關于經紀合同期限問題,建議約定3年期滿后,雙方如能達成一致,可協商續約3年,如無法達成一致則經紀合同期滿終止。考慮到經紀公司基于利潤回報等問題通常會簽訂較長期限的經紀合同,藝人幾乎沒有可協商的可能,建議可以與經紀公司協商約定在超過幾年以后,符合一定條件的情況下,藝人有權提前終止合同,例如藝人為經紀公司帶來多少收益、歌手已經灌錄多少唱片、演員已完成一定數量的影視作品等。如此約定至少已考慮到經紀公司的前期投入與后期收益問題,雙方有協商達成一致的可能,藝人也不必為了自身發展,即便承受高額違約金也要解除經紀合同而與經紀公司對簿公堂。


